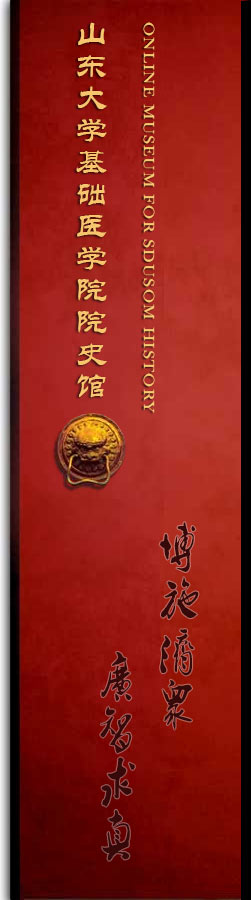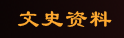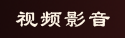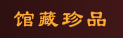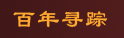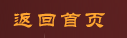五、名 人 逸 事
五、名 人 逸 事首页 > 文史资料 > 名人逸事
|
梁启超结识栾调甫 |
|
栾调甫,我的父亲,是本世纪研究我国古代学术的一代学人。他出身小伙计,有不足五年的学历,却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。他有许多奇闻轶事,有的书上说他是“一应奇特之士”。他早期苦心钻研墨学,被学术大师梁启超誉为“石破天惊之发明”,被文史学界称为“当代理墨名家”,“自孙仲容以后的第一人”。他以40年的精力,献身于我国文字学的研究,书刊上评价他“创立《字系说》,贡献最大。”他对《齐民要术》作了三大考证,50年代,被农学界称赞为“《齐民要术》研究开创之人”,“贾学第一功臣”。尽管可以从昭和15年日本出版的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中查到栾调甫(1889~1972)的名字和简历,还可以从一些文史书刊、资料中读到有关他的论述和评介,但是,平时却很少能从人们的口述中听到他。至于栾调甫的名字不为人所知的缘故,正如1982年12月21日《济南日报》刊登的袁兆彬写的《长眠英雄山下的一代学人》短文所说: “提起来栾调甫,许多济南人恐怕也未必知道,这原因,我想一方面是他研究的学问太专门、高深;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“性格高洁、不求人知。” 是的,正由于父亲性格高洁、不求人知,因此,也就鲜为人所晓了。这使我忆起梁启超与父亲相结识的一段趣闻故事,一位知名度特高的大人物与一个不求人知、鲜为人晓的小人物,在探索祖国古文化的征途上不打不成交之后,并肩作战,成了亲密的同志和战友。 那是20年代初的事,学术大师梁启超耗费了20余年的精力研究《墨经》,写了《墨经校释》一书(商务印书馆出版),在当时墨学界颇有影响。书出版不久,梁启超极其意外地收到一份专事抨击、批驳他这部大作的文章《读梁任公墨经校释》,而文章的署名却是一名闻所未闻的栾调甫。梁任公读了这篇文章,大为震惊,一来是,过去从未有人敢这样评批他的著作;二来是,海内治墨界中,竟有超越他的“小人物”,梁启超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个栾调甫,一睹其人,探个究竟。 就是这个为梁启超急于寻找的栾调甫,自15岁立志整理国故开始,就对墨子书发生了兴趣,用父亲的话来说:“《里经》是子书中有名难读的几篇书。……但是,因为难读的缘故,越足引起学者研究的兴趣。”后来他的兴趣与日俱增,发展到废寝忘食、入迷的地步。他薄视一切人间事,隐身到诸子百家故纸堆中去,读尽历代所有版本的墨子书和古今中外所有论述墨学的论文、著作。当得知梁启超出版了一本《墨经校释》,父亲喜出望外,迫不及待地以能早睹为快。后来他托上海的一个亲戚购得,拜读之下,大失所望,对梁任公书中的校释,颇多异议。父亲认为“本书最大的缺点,是校释内随意改字、删字的办法。”此时,父亲研究墨学已是20个年头(1903~1922),造诣颇深,他那后来为学者们大为赞赏的《名经注》早已脱稿,但他从不喜欢出头露面,一直未曾发表过什么文章。此时此刻,他看到梁启超任意窜改、歪曲《墨经》,觉得势必贻误后人,就再也耐不住性子,在那六月天里,挥汗不止,连夜赶写成《读梁任公墨经校释》一文。这是1922年的事。 这篇文稿,父亲亲手刻板、油印了40份,分发给海内同治是学的专家、学者,一行行竖文,毕恭毕敬,深深体现他那一丝不苟的精神。只是,我那生活在旧社会里,善良而又安分守己的母亲,不同意父亲去写那些批驳别人错误的文章,特别对待梁启超的大作。梁启超的大名,她是从课本上知道的,梁启超的事迹,是在课堂上听到的,对于这样一位学识渊博、誉载四海的人物、权威人士,更不能有损人家的面子,以免招惹是非。可父亲不听母亲的劝告,还是把自己的批驳文章寄出。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型刊物《东方杂志》在接到父亲那篇《读墨经校释》文槁后,不敢刊登,即转交给梁启超审阅。父亲对此不以为然,日后,他在《复王君景宋书》中写道:“学术之有进步,全在严格批评,不但纠正原书过失,免致遗误后学,且可促起作者警觉,使之慎重厥事。古来不少误说,……”是的,必要的批评还是应该的。 1925年暑假里,父亲返回家乡蓬莱省亲,把自己写的《读墨经校释》油印稿和梁启超的亲笔信交给爷爷看,二姊说:“那时,我也在爷爷屋内。爷爷看完以后,指责父亲没有学者风度,说什么可以批驳别人的错误,但不需要显示自己的名字,这真是趣事。当时爸爸没有说什么,我心里有点莫明其妙。后来,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,即写书为的明教世人,非为个人荣誉。”诚然,父亲自幼是遵循爷爷这一教导的,写文署名,本是正常的事,不足为奇。父亲著书立说写文章之所以署名,不是为了别的,而是胆敢认真负责,不顾个人得失,不畏权势,不询私情,不因梁启超之尊,而随声附和。他只知求真求实,而不求人知晓,所以,发给梁启超那份油印稿,照样也是孤另另的一份文稿,而不另作一书一字,正像梁任公日后给父亲的信函中所说的:“函内无书,又无发函地所,怅惆不可言。”这个栾调甫,何许人也?何处可以寻见?只凭借文稿中“栾调甫”和邮戳上“济南府”六个字,梁启超不无海里摸针之感! 那时,父亲居住在济南山水沟,那个在旧社会颇为人们唾弃的小地方,蛇街陋巷,狭窄泥泞,茅舍草棚,低矮拥肿。正由于此,山水沟在济南倒也成了块知名的地方。父亲在这里租赁住房一间,半边是灶屋,半边是小土炕,一家五口,夜里挤在上面睡。象这样的地方,这般家景是没有人会来串门的。那时,父亲在齐鲁大学博医会当编译员,整天家洋文来、汉字去地翻译、编辑着,像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,也不会被入理采的。莫说是远在天津的梁启超无处打听,就是近在眼前,已经就学齐鲁大学,父亲同一个学校的孙碌,急于求见父亲,也没有打听到。这位后来成了父亲的学生,日后又活跃在文史界的孙碌,之所以急于求见父亲,是受其同乡世伯、墨学家张子晋的忠告:“齐东栾调甫先生,识弘才隽,为当代理墨名家,苟相值,务师之,足裨汝前途也。”以后,他之所以找到了父亲,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是在学校图书馆借书证存根上发现父亲的名字而找到的。梁启超之所以能打听到父亲,也是天公作美,有一定的偶然性。1925年,梁启超去上海,得知湖北的张仲如,言谈之中,得知父亲藏身之处。张君是1920年父亲初到济南,在江镜如博士家中认识的,仅一面之识,至父亲的《读墨经校释》问世以后,方有学人之交。 梁启超返回夭津后,旋即给父亲写了亲笔信,一封中式信封,下款印着“天津意界玛尔谷路二十五号梁缄”字样的挂号信,信封上清晰地盖着“天津府,十四年五月十四”。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: “调甫先生:两年前,曾得邮寄尊著《读墨经校释》油印稿,读之頫首至地。” 这里所说的“两年前”是指的1922年6月,也就是说梁启超花费了三年的时光才找到父亲。 这篇《读墨经校释》发表以后,隔年《东方杂志》又登载了父亲的《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》一文,这两篇文章犹似两只铁拳呈现在墨学界,被人传之为“栾师两打梁任公”。诚然,父亲是毫无打击梁任公之意,他的《读墨经校释》只是有理有力,但却又是极其谦诚地论证粱任公的差错,毫无妄自尊大之心,正象父亲所说的,“(一)校释完全与我相同的,不必讲;(二)校释的理由,虽觉可信,但我一时尚未完全领悟的,不能说;(三)校释的理由,虽觉不充足,但我一时尚未能彻底指证的,不敢说。这三个条件,前一,有我作的《名经注》在,后二,唯有等着我能领悟,或指正的时候,再来请教吧!”父亲的这“三不说”,四川学者伍非百深有感触地说:“可见栾君对于著者、读者虚心与诚意了。余愧不如栾君之谦怀,苟有所见,辄说说不已。” 不仅如此,父亲多次、多处地对梁任公深表敬重,他对于梁任公“这样长期研究的精神,实在是非常敬重。所以现在本着我敬重的心意,愿把我读这书不同意的地方,与我认为是缺点的,一一写出来。”“假定我说的完全无误,那原书著作的价值,仍然存在。那是他著作的精神,也靡有丝毫可以轻藐的,”“所以,我读这部《校释》,虽有些不满意的地方,但我对于作者这番勤力,却是自始至终,只有敬重,而无丝毫轻藐的心,就是读我这篇的读者,对于本书亦当如此。” 父亲一贯坚持以理服人,反对以势压人。以反映我国古文化的真实面目为宗旨,也反对那种抓住他人的一些错误不放,一棒子打死,来提高自己,父亲在给张仲如的论学信札中,可以透视他这一点:“其实余于任公之作,并不薄视,且极推重之,如牒字例,辩无胜解,皆极精确,……今之少年,好祗诃前辈,摘人疵累以为快,此种风气不除,殊非学问前途之福。竞念不除,学问必不能臻绝顶……真学问家,非徒无竞念,亦不知有人我也。”梁任公也很谦虚,他读了父亲那篇《读墨经校释》后,自检一过,认为,“我自己也将十年来随时杂记的写定一篇,名曰《墨经校释》,其间武断失解处诚不少。”他称谓父亲,“今世治先秦学者多矣,既能入,又能出,所见未有如公者。”在他的信函中,和日后的文章里对父亲的评论和称赞,以及在学术探讨上的那种服从真理,尊重他人的高尚品德,实不愧为一位著名的学者。 梁任公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:“燕齐咫尺,何时能奉手商量旧学?”随后,他不耻下问,专程来到济南会见了父亲,这时,父亲早已迁居齐鲁大学。这座由洋人办的洋学校,洋人身居那些不同格调的大洋房,中国人却住在统一规格的小平屋。当梁启超走进东村五号父亲住的小平屋里,以极其兴奋的心情会见了那不求人知的“小人物”。他带有神秘感环顾了一番这座房舍,室内四壁,顶天立地数不清的古旧书籍,墙脚是成堆的文稿、故纸,即连卧室也是到处堆着书册,除此之外,只有一张没有抽屉、退了漆色的四方桌。父亲日夜俯案书写,写下了上百万言的文稿,今天,也就是在这张桌子上,梁启超与父亲进行了难得的畅谈。梁启超似乎已感触到,在这死寂的乱书窝五号住宅中,却蕴藏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藏,因此,他直接了当地提出来济南求见父亲的第二个目的,那就是要聘请父亲去北京燕京大学任教,共商旧学,他说那里可以为父亲提供优越的研究环境和条件,而且可以享受超出父亲现薪六倍的高薪。父亲婉言谢绝了。梁任公的济南之行虽然未能聘请到父亲,但能会见这位“性格高洁、不求入知”的一代学人,而且得以畅谈数日,他也就心满意足了! |